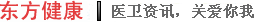我不能具体地告诉你,沈同庆是干什么的,甚至也不能够将他真实的名字写在这里,因为他很有名,在他那一行里,他绝对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我们的相识缘于一次采访,采访结束的时候,沈同庆从他阔大的办公桌后面向我伸出修长的手臂,他握住我的手,说:“你很有思想,接受你的采访很开心。”他抿嘴微笑的样子,真是迷人,使得我走在回去的路上时,还在回味不已。
之后,我们成了时常通电话的朋友,准确地说应该是“忘年交”——他比我大了整整18岁;在他对我说出文章开头的那句话之后,我成了他的情人。我们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是在他办公室的蓝色地毯上,激情过后,他将脸埋在我的胸口,喃喃自语:“我很累、很累,别人只看到我的风光,没有人体谅我承担的重负,人在江湖,多少明枪暗箭……有时候我真想放下这一切,去新西兰,买一片农场,做一个农夫……”我的心在那一瞬间被一个男人的脆弱和孤独击碎,我再度拥紧了他,说:“我能理解的,我会陪在你身边,永远。”
做情人和做妻子的最大不同是妻子可以挽着爱人的手走在阳光下,而情人只属于黑夜——更何况是做沈同庆这样一位公众人物的情人。我们不能随便通电话,不能一起出去吃饭,不能并肩走在大街上,甚至不能在宾馆开房间……可是也因为这种种不能,让我们的爱更富于刺激更让人过瘾。
我是个最懂事的情人——不要钱、不要名分、不多问、不吵也不闹。我彻底地付出我自己,并在这种付出中获得快乐和满足——也许人真的是自虐的动物。“我的小傻瓜”,沈同庆喜欢吻着我的额头,这样叫我,也许我真的是够傻的,将他这句话理解成:这样委屈你我很心疼。
我想沈同庆是爱我的。比如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之后,他向在座的记者们挥手告别,记者们笑着赞叹:“沈先生真有风度。”只有我知道,他挥手,只是为了让我看见他腕上的那只手表——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比如情人节那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下班以后,你径直往海淀路口走,在海淀宾馆大门的右侧,有一个废弃的烤红薯的大铁桶子,你去看看那里面有什么。我按照他的指引,果然有一只大铁桶,一掀盖子,发现了一把鲜艳欲滴的玫瑰——真难为他是怎样费尽心机才将花事先藏在这里的;比如那一次次畅快淋漓的肌肤之亲,他在我耳畔的喘息,他拥抱我时的力度,他抚摸我时的触感……都让我相信:他,是爱我的。
日子原本就可以这样继续下去,痛苦和甜蜜,委屈与幸福,种种滋味夹杂着,充实而令人兴奋。可是,我怀孕了。我想要这个孩子,这是我和我深爱的男人的结晶,也会是我后半生的寄托,他有资格到这个世界上来不是吗?也许他永远不会有一个合法的父亲,但那又有什么关系?我有能力抚养他,给他好的教育,在他长大以后再告诉他谁是他的父亲……我想了很多,关于做一个单身母亲种种可以预见的困难,惟独没有想到沈同庆会不同意我要这个孩子,理由是他不能容忍自己的亲骨肉生活在别人的有色目光之中,我们第一次起了争执,最后他说:“亚妮,你怎么这样不懂事?”那声音冰冷,而高高在上,让我如此的陌生。
最终,我还是去医院做了流产,独自一人。我躺在冰冷的手术床上,锥心的痛。沈同庆直到第三天才来看我,他抱着我,说:“你受苦了。”我将脸转到一边去,泪水大滴大滴地落下来。我咬着牙,将任何一句埋怨的话活生生地从嘴边咽回肚里,我告诉自己:谁让你爱他?既然爱他,你就要承担得起这样的命运。
作为一位公众人物,沈同庆自然很忙,他有限的时间大部分给了他的事业,剩下的部分七分八分,属于我的少得可怜。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寓言故事里那个守株待兔的笨蛋,永远被动地等在同一个地方,一切听凭运气——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在他不来的时间里,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那些独对孤灯的漫漫长夜,我抱膝坐在床上,听着墙上的钟一格一格地向前走着,内心烦躁不安,像一只困兽,随时都有咆哮的可能。我渐渐失控,不能自禁地一次一次要求他:“可不可以多陪陪我?”在我第N次向他提出同样的要求时,沈同庆对我说:“亚妮,的确,你一个人太孤单了,我不能太自私——如果有合适的男人,我不希望你因为我而错过——”
他这样对我说的时候,世界在一瞬间失去了声音和颜色,我仿佛置身荒原,心以极其缓慢的姿态往下坠、往下坠——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什么?让我再找一个男朋友吗?他烦我了?他想退了?他不爱我了?如果他还爱我,他怎么会对我说这种话?他把我当什么了?一件随时可以转让的物品吗?我大睁着眼看他,嘴里却说不出一个字甚至不能发出一点声音。
那之后,我时常会无端地陷入恐慌,就像是末代皇帝,一直以为自己天下在握,却渐渐发现其实什么也做不了主什么也控制不了——那种深深的没有着落的恐慌。他的心正以令我陌生的漠然渐行渐远……
接着就是春节了,无数的人为了一张火车票想尽各种方法,只为了在这个节日可以阖家欢聚,北京在转瞬间几乎成了一座空城。我没有回家,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我怕回家又得面对亲朋好友们的老问题:“亚妮,什么时候将男朋友带回来给我们看看呀?”
除夕之夜,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窗外寂寂闪烁的都市霓虹,巨大的孤独和无助袭击了我,我给沈同庆打电话,说:“你来看看我好吗?我一个人,心里特别特别难受。”他显然是不高兴的:“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今年春节我要回老家的,我不在北京。”他将电话挂了,我又打过去,他再挂,我再打,如此反复,我像疯了一样,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也顾不得尊严,流着泪,苦苦求着一个男人:“来看看我,好吗?”直至他的手机关机。
大年初一,我决定慰劳一下自己,去国贸的茶餐厅吃饭,一进门,就看见了沈同庆,身边的应该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吧,三个人正头靠头对着一本菜单研究点什么餐。他的妻子盘着发髻,黑色的毛衣,恰到好处地搭配着一条桃红色的围巾,托着腮微笑着,一眼看去就是那种被家庭保护得很好的女人;他的女儿,有着一头乌黑的长发,时不时娇娇地嘟嘟嘴,似乎在说:“我不想吃这个。”一家三口,丈夫成功、妻子优雅、女儿可爱——多么和谐的温暖的画面!而我,我是什么?我算什么?
在那一刻,我领悟到一个真理:一个男人,他可以对你蜜语甜言,他可以和你缠绵缱绻,但在他内心深处,真正在意和看重的,还是他的结发妻子和他的家。
我一个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泪水流了一脸。一直都以为,我是在为一份纯粹的爱、一位值得爱的男人付出,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三年的青春、三年的牺牲,全都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到头来我却发现:所有的不过是我自己给自己制造的一场梦境,沈同庆,他爱过我吗?或许,曾经爱过;或许,从来就不曾,我只不过是他工作之余的一场情感消遣而已——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摧毁我,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激起我破坏一切的欲望。
回到家,我拿出纸和笔,给沈同庆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简单:你骗了我,现在我要你付出代价。我要钱,20万,否则,我会将那些照片公布于众。那些照片,是我和他的家居照,我用数码相机拍的,为的是他不来的时候,可以凭借这些照片感觉到他在我身边。我满怀着爱意拍了那些照片,而现在,它们却成了我发泄恨意的工具——多么荒谬的讽刺!
沈同庆在收到我的信后约我去他的办公室,在那间我们有过无数次鱼水之欢的办公室里,在我将存有那些照片的相机内存卡交到他手里之后,他将一张20万的支票放在了我面前,神情倨傲。他说:“亚妮,20万对我不算什么,我只是没有想到,原来你也不过是一个这样的女人。”
是的,20万对于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而20万对于我,更不算什么——我的心伤,我梦想的幻灭,岂是20万可以补偿得了的?我以为这20万可以稍稍化解我心里的不平衡,却发现那根本不可能,真正因为这20万获得心灵安宁的人是沈同庆,一句“原来你也不过是这样的女人”,轻易地将我和他割开,将曾经的男欢女爱一笔勾销,他轻轻松松全身而退,而我,却要在每一个孤单的夜里,像一只受伤的狗,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地舔着伤口——我输得是这样彻底。
然而不管怎样,生活还是会一样继续,我只是学会了自嘲:一直以来,我近乎自虐式的忍耐,只期望自己能做一个对方眼中完美而脱俗的情人,可是到头来,在他的眼里,我和娱乐圈里那些拿着所谓的录音带去要挟导演的三流女演员并没有什么区别吧?
画外:也许每一场见不得阳光的爱情,总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纯纯粹粹轰轰烈烈,可是到最后各自亮出的底牌,无一例外的恶俗不堪。就像是一场盛宴,一路吃下来、吃下来,终也成了残羹,无可避免,无法收拾。